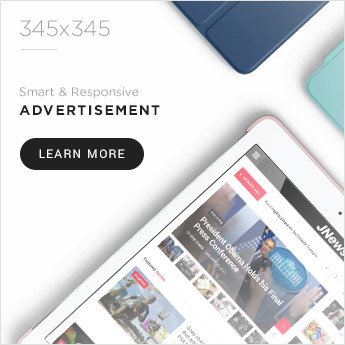(文/林思遠)歡迎您來到「華州城市巡禮」。今天我要給您介紹的這座城市,雖然是普吉特灣地區的第二大城市,華盛頓州的第三大城市,但卻長期被西雅圖的光芒掩蓋,往往不為人所知。它就是Tacoma。
華盛頓州的最高峰,山頂積雪終年不化的雷尼爾雪山/Mount Rainier就坐落在距離Tacoma 70英里的東南方向。從雷尼爾雪山/Mount Rainier西側流下來的涓涓細流匯集成Puyallup River,在入海口沖出一片三角洲,最終流入普吉特灣。正是在這片三角洲上,美洲土著居民Puyallup部落在Tacoma地區繁衍生息了幾千年。
時間來到19世紀。1841年,美國海軍上尉(Lieutenant)Charles Wilkes從Puyallup River的入海口開始探索普吉特灣海域,於是就給Puyallup River入海口的海灣命名為Commencement Bay,Commencement在英文中就是“開始”的意思。
Wilkes上尉只是來考察了一番。第一位Tacoma地區的歐洲居民是來自瑞典的Nicolas Delin。1852年,他在一座小溪邊建了一座水力鋸木廠,也慢慢吸引了一小批人來到附近定居。然而好景不長,僅僅三年後,本地美國人和印地安人之間的戰爭爆發。大大小小的衝突在普吉特灣地區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Delin的鋸木廠在戰爭中被廢棄,剛剛建立起來的社區也化為烏有。
戰爭過去之後又過了將近十年,一位內戰中的退伍老兵在Tacoma建了一座小屋,圈了一大塊地,然後賣給了開發商Morton McCarver,發了一筆財。這座小屋後來成了Tacoma市的第一座郵局。McCarver把買下的地命名為“Tacoma City”,並開始遊說國會,希望將Tacoma作為即將開建的北太平洋鐵路(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西部的終點。北太平洋鐵路從明尼蘇達州開始,自東向西橫貫大半個北美大陸。1873年,McCarver的遊說發揮了作用,鐵路的終點選在了普吉特灣,但車站卻建在了當時的Tacoma市以南兩英里的地方,為了表示區別,車站附近被稱為“新Tacoma”。1884年,新舊Tacoma合併,三年後,北太平洋鐵路開通。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鐵路的開通對Tacoma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880年,Tacoma的人口還只有1,000人。到1890年便暴增到36,000人,十年間增長了36倍。
19世紀末的淘金熱吸引了很多人來到西海岸,其中也包括數以萬計的華工。這些最早踏上美國土地的華人在這裡開餐館,修鐵路,伐木,淘金,巔峰時期的人口超過十萬。但這些華人享受不到美國公民的待遇。許多美國人認為這些華人不僅搶了他們的工作,還搶了他們的金子。於是當時的美國,特別是西海岸地區的排華情緒日漸高漲。在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的背景下,1885年,Tacoma市政府勒令所有華人在11月1號之前離開Tacoma。11月3號,所有還在城中的華人被強行驅逐到火車站,送到波特蘭。幾天後,整個華人社區被夷為平地。這種暴力驅逐本地華人的方法被稱為“Tacoma方法(Tacoma Method)”,在西海岸的各個城市廣為流傳。1896年,晚清重臣李鴻章在訪問美國期間,強烈批評了美國的排華運動。在結束美國東部的訪問行程之後,李鴻章選擇從加拿大溫哥華啟程回國,繞過了美國西海岸地區,以示對西海岸排華運動的抗議。
進入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Tacoma的進一步繁榮,城外有了美國首屈一指的賽車場和好萊塢之外最大的獨立電影製片場地。選民還投票支持購買了附近七萬英畝的土地用於建立美軍軍事基地。但隨之而來的大蕭條沈重打擊了Tacoma。在1929到1930年的那個寒冬,Tacoma經歷了大規模的停電,甚至動用了停泊在港口的萊克星頓號航空母艦的發動機來給Tacoma供電,其蕭條程度可見一斑。
讓Tacoma重新煥發生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人,水手和工人蜂擁而至,軍事工業欣欣向榮。二戰過後,Tacoma城內的重建和擴張喚醒了人們保護老建築的意識。舊的市政大廳免於了被拆除的命運,在整修後變成了政府的辦公樓之一;聯合火車站(Union Station)變成了法院大樓;一個舊報社的大樓成為了華盛頓大學Tacoma校區的教學樓;舊的音樂大廳成為了新建立的劇院區的中心,等等等等。在Tacoma街頭轉過一個街角,眼前的一磚一瓦都可能是歷史的見證,等待著你去探詢它背後的故事。